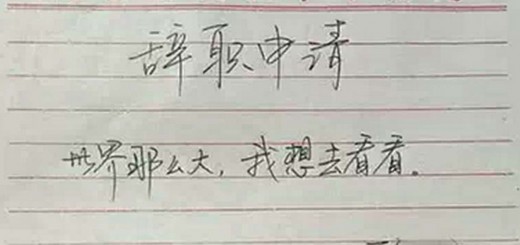文/林少华
也是因为近日的广西玉林狗肉节闹得沸沸扬扬,我再次想起了我养过的一条狗。那是一条极普通的狗。它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得只能说是普通的狗。
那也是我养过的惟一的狗。大体是我在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一期间养的。当然不是作为宠物养的——连宠物为何物都不晓得——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夜间需要有个动静壮胆,就养了一条看家狗。黑毛,眼睛上边各有一小块白毛,俗称四眼狗,我和弟弟给它取了个很威风的名字:虎虎。虎虎命苦,从来都吃不饱肚子,总是瘪着肚子在地上到处嗅来嗅去。这也怪不得我,怪不得我们家,因为我们也基本吃不饱肚子。父亲倒是挣工资,但在离家百里之外的一个公社工作,一个月四十七元伍角,八口之家,且两地分居。有一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把家属下放农村,于是母亲和我们兄弟六个就像图钉一样被死死按在了那块半山区的沙土地上。穷得连口粮都领不回来,偶尔吃到一两块猪肉,香得我和弟弟差点儿抱着脑袋晕倒在地。虎虎当然就更可怜,能喝到一口刷锅水就大喜过望了。因为刷锅水要喂猪,年底卖猪换口粮。
狗不嫌家贫。虎虎从不到别人家去,就那么瘪着肚子看家护院。我和弟弟上山打柴它就跟着。冬天放学后,我和十来岁的大弟弟拖着我们叫爬犁的雪撬出门。过了铁道,过一条河,再过一片庄稼地和荒草甸,一直往南走去,进了山还要往里走很远才能找到干树枝。虎虎一路跟着我们,或前或后,或远或近,或快或慢,回头回脑,屁颠屁颠的。东北的雪一点儿都不含糊,动不动就深过膝,越往山里越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用绑在长竿上的钩刀钩树枝,弟弟跟在后面拣,拖回放爬犁的地方。钩得多了,我就跟弟弟一起拖。大多是从坡下往坡上拖。拖着拖着,天就麻麻黑了。空旷的原生杂木林,除了雪就是树,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偶尔传来的猫头鹰叫声和撕过树梢的寒风,什么声音也没有。虽说习惯了,但我和弟弟终究是孩子,还是有点怕。怕了就叫“虎虎——”。也怪,每次虎虎都不知从哪里飞一般应声而至,歪脑袋蹭我们的腿,伸舌头舔我们的手,甚至立起前肢亲我们的脸,眼神乖顺、温和而又凄惶空漠。我们搂住它的脖子,把冻僵的手伸到它脖子的毛里取暖。有时脚一滑,就一起在雪中滚下坡去。
下山天就更黑了。出了山,下坡没了,爬犁重了,我们望着远处自家如豆的灯光,像纤夫一样一步一挪。大概盼着回家吧,下山时虎虎一直颠颠跑在前面。跑出很远又跑回来,但见月光下白皑皑的雪地里一道黑影由远而近,三两下就蹿到跟前。那时候我觉得虎虎是那么矫健,真个虎虎生威。有时候显然跑到家了,又放心不下似的折回来接我们。这回不再远跑,摇晃着更瘪的肚子,几步一回头在前面带路……
后来不知为什么,它开始追鸡,追得鸡扑楞楞满院子跑。再后来的一天,当我从八九里路外的学校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村里两三个大人正从门前山脚一颗歪脖子老柞树上往下放一条吊起的狗——虎虎!我没跑上去,没问什么,也没有回家,背着书包直接走去山的另一坡,靠一棵树蹲下,脸伏在双膝间一动不动。我一边默默流泪,一边想虎虎从来不曾鼓起的肚子,想它细瘦而温暖的脖颈,想它冰天雪地里朝我奔来的身姿和眼神……我的苦命的虎虎!
此后我再不养狗,虎虎成了我生命旅程中的一个惟一,一个定格。